本帖最后由 沪上襄阳人 于 2014-8-14 19:23 编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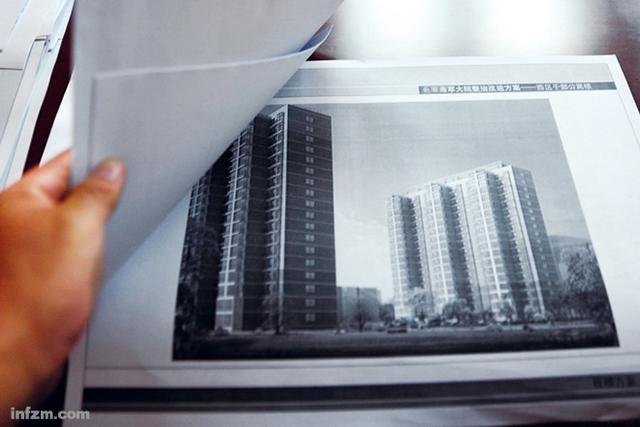
一名军官拿着北京某部队大院整治改造方案,期盼住上干部公寓楼终于有了眉目。

北京解放军某部离退休干部住房建设小区工地,被强制拆迁的“钉子户”看着自己的房屋被推倒。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的军队“清房”行动,大多“雷声大、雨点小”,鞭子高高举起,却轻轻落下。这一次的清退战能否走出运动式的轮回? 参加军队清房动员会议归来,某军队“清房办”工作人员张清印就在台历上划了三个红圈:6月30日前,组织自查自纠,“把住房、用车情况向组织上说清楚、交明白账”;8月31日前,全面完成“清房”工作;10月底,全军将组织综合检查验收。 2014年5月30日,解放军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、总后勤部、总装备部、军委纪委联合发出通知,要求各级单位“清房、清车、清人”。 与以往历次“腾房”运动不同,“这次要动真格的”。最近这两个月的讲话中,四总部的领导多次下达“清房”敦促令:凡是隐瞒实情、拒不整改的,将点名道姓向全军通报。对工作不力、进展缓慢的单位,将严肃追究相关领导责任。 从此,张清印就陷入了入夏以来的持续焦躁中:眼看着日子正逼近第二个“红圈”,却还有“不少难啃的骨头”。 “难啃的骨头” “清房”之所以棘手,正是因为复杂的裙带关系,违规占房者要么是“关系户”,后台很硬不好碰;要么则蛮横无理,惹不起;也有部分经济和生活困难户,不忍心“赶”。 对“钉子户”多次劝说无效后,今年7月初,张清印决定对战友余某“上手段”。 “他是我的战友,还是老乡,我心里很难受。”一个月前,张清印第一次登门劝其退房,一番寒暄之后,硬是被余某的爱人推出家门。 2005年,余某以副团职干部身份自主择业,部队多次劝“腾房”,余某则以孩子就近上学为由,赖着不走。 “这次要动真格的。”第一步,收回余某车辆出入证,也不允许其孩子乘坐部队的通勤车上下学。紧接着,部队派出水电班,断电、断水、封门。为免出现法律纠纷,“清房”现场还有人员肩扛摄像机全程取证。 麻烦随即而来,在京工作的几个山西老乡纷纷打来电话,希望能“放一马”。说情者甚至包括张清印的姐姐,“弟,你不能做得太过啊,以后还怎么回去面对乡里乡亲?” 为了对抗“清房”,余某则准备了饼干、方便面和几大包蜡烛……如此坚持一月有余。最终,在居委会威胁将停发社保金,以及辖区派出所的介入下,余某才将房子腾退了出来。 “清房”之所以棘手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复杂的关系,违规占房者要么是“关系户”,后台很硬,不好碰;要么则蛮横无理,惹不起;当然,也有部分经济和生活困难户,工作人员又不忍心“赶”。 以往部队“清房”的指导思想是,和谐与稳定压倒一切,倘若违规占房者置之不理,工作人员就无计可施,鲜有强制“清房”的行动。 “这真是得罪人的苦差事。”张清印说,当初,很多干部宁可选择下基层部队“蹲点”,也不愿去刚刚组建的“清房办”。对抗激烈之时,工作人员家门上的春联会被人喷墨水,或者门前被莫名其妙地扔上一袋黑色垃圾,甚至有“钉子户”干脆带着铺盖卷,横躺在工作人员的家门口。 驻守东南沿海一线部队的团长周韬第一次上门做说服工作,眼角就遭对方“破相”,用大墨镜遮了半个月。 周韬调查发现,该部出现的违规占房者大多是“军二代”,也就是离退休或转业干部的子女、亲属:该部队工程师黄某已去世多年,其宿舍却被女儿转租出去,“难怪附近航空公司上班的空姐总是出现在家属院内”。 很多部队老干部在其退休或逝世后,住房由其子女继承,或居住,或转租,甚至出售。二手房市场上或租房网站上,不乏“军产房代售”、“军产房代出租”之类的广告。 “清房办”工作人员要求黄姓女子退房时,却被告知“没有房子住,拒绝腾退部队宿舍”。通过查证地方政府房管部门的档案,该女子原来在当地还有两套商品房。随后的强制“清房”过程中,怒不可遏的黄姓女子把周韬的脸抓破了。 “清房”干部苦不堪言,而不少违规占房者也满腹牢骚,认为自己才是“受害者”。 “从潜艇部队,到雷达站,我把人生最好的二十年都留在了部队,最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”家住青岛某部队的老蔡因强烈抵制“清房”,而得绰号“老赖”。 老蔡的妻子诉苦:1999年,老蔡转业“不逢时”,正赶上地方政府的房改,停止福利分房,青岛的房价却一天天高涨,自然买不起商品房,一家三口只能赖在六十多平方米的部队宿舍楼里,几乎年年都要忍受“清房”之苦。 今年6月底的一天,老蔡的妻子接到邻居电话:“快回家看看吧,撬你家的门了。” 匆匆赶回部队家属院,铁制防盗门已被撬开,家电家具等整齐地摆放在大院的操场上,大衣柜上还贴有一张纸条,写着老蔡的名字。 “我走南闯北的时候,你在哪里?”“党性?我干了一辈子的革命。你跟我讲党性?你敢不敢和我讲功劳?”“清房”工作中不乏这样的对白。 “树活一张皮,人活一张脸。”张清印说,这些只是极端的个案,多数违规占房者最终还是接受部队的“清房”决定。 凡是积极主动退房者,部队也会施以“援手”:免费派出人员、车辆协助搬家:大热天,战士们爬上爬下把空调、太阳能热水器等拆卸、安装好,再帮助老人调整好电视信号系统。对于经济特别困难的退房者,部队还会适当发放一笔安家费。
“清房”影响着战斗力? 这几乎是全军普遍的难题:部队宿舍被违规占用,而符合分房条件的官兵却难以申请到住房,只能自己买房或在外租房居住。 “能否给两年时间腾退?” “对不起,这是上面的规定,必须在8月底清退完成,望首长配合。” 《解放军报》2014年5月18日的报道说,浙江省军区一名原副部长,现已转业到地方环保厅任职,却被发现除在省军区占有一套老式住宅外,原来任职的湖州部队也有一套住房。 相较于过去,这场“清剿战”,作战范围稍有扩大,不再局限于以往离退休和转业干部。 “现役级别较高的干部,比如军以上干部,往往由于工作调动的原因,他们会有多套房产,超面积的情况也比较严重。”原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陈先义介绍,例如一名高级军官从广州调到上海,迫于颜面,广州部队不敢收回其房产,这导致“多地有房”现象尤为严重。 2014年5月,四总部的通知对领导干部“多地占房”等违规现象,有着特别的“关照”:军职以上干部装修期超过一年半、师职以下干部装修期超过一年原住房仍未腾退者,必须坚决予以清退。 对于领导干部群体而言,以往护身的“尚方宝剑”,这次难以抵挡高悬头顶的反腐之剑——主动“说清楚”、“交明白账”,辅以督导整改。正是因为事关军中前途,“清房”一声令下,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主动上报,退还违规占有的部队房产。 地处保定市中心黄金地段的100号院,是北京军区保定军分区有名的家属院。2006年,在老营区内部,部队以高标准修建了100号院。当时,在职机关领导干部和退休老干部,包括地方一些领导都各自分得一套房,剩余房子还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对外出售。 军分区司令员江永亮、政治部主任李大忠各自分得一套165平方米的房子后,他们又花钱购买了一套小户型。“清房”令下达后,二人住进军分区招待所,主动退掉军分区分配的大房子,以及自己花钱购买的小户型,各自还搭进去近10万元装修费。 “不舒服归不舒服,违规的事情当领导的必须先带头改正!”《解放军报》5月29日援引江永亮的话说。 “清房”之后,几家欢喜几家愁。 春节过后,广州军区空军某基地营区的公示栏内,张贴着刚清理出的两套住房的分配情况,两名机关干部兴高采烈地领到了宿舍钥匙。 这几乎是全军普遍的难题:部队宿舍被违规占用,而符合分房条件的官兵却难以申请到住房,只能自己买房或在外租房居住。 最近几个月,陆俊杰都会到西三环某部队大院的公示栏旁走上一圈,留心是否“榜上有名”。 1999年参军到北京,虽然调整为副营半年有余,已符合部队分房条件。但是,看到该部队后勤部门的待分房名单上,陆俊杰突然意识到,“看来是没戏了”。 这份待分房名单上,按照职务、军衔、军龄以及婚姻等实际指标排队打分,从高到底依次排列着几十号待分房人员名单,不乏“有家有口”的团级干部,也只能在外租房,而部队的家属楼却被很多陌生人居住着。 “房子问题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建设,影响了军心士气。”张清印说,部队中不少年轻人主动选择转业。 陆俊杰也曾两次打报告申请转业。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卫星遥感专业,属部队成功引入的地方大学生,当年,一度被《解放军报》等多家媒体以典型广为宣传,岂能允许“典型”离队? 繁华的北京西三环地带,对于陆俊杰来说,房子不仅是栖居之处:同女友已相处多年,女友家人要求要想结婚必须在京有房,为防止女儿偷偷结婚,准丈母娘硬是把户口本锁在家里的铁柜子里。陆俊杰来自农村、每月不足五千的工资,购买商品房并不现实。后来,准丈母娘做出妥协,部队有住房也可结婚。 “房子已成为年轻军人扎根部队的一个重要部分。”副团级女干部刘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2012年冬天,从位于北京北部昌平区的某场站调到总部机关后,大院住房紧张,刘蓉一家只能居住在原单位分配的宿舍内。 “每天上下班急行军。”刘蓉描述说,清晨六点一刻,叫醒孩子起床,一起坐上开往大院的通勤车。八点前,把孩子送到大院内部的幼儿园,再匆匆骑上自行车赶往办公室……下午五点半,再赶到幼儿园接孩子,坐上回场站的通勤车。其间,难免遇上北京晚高峰的大堵车,最通畅的纪录是晚上八点回到家。 “妈妈,我真的很累。”一次,四岁的儿子坐在班车上说完这句话,就睡着了。刘蓉说,倘若年底再分不到住房,将考虑主动申请转业。
|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