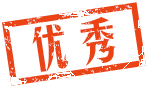短篇小说(字数:6350)
在我们小区跳舞的广场,常发生有趣的故事。这不,王腊狗,这个六十岁出头,就连名子都是土拉吧唧,顶没才艺像的乡巴佬,今天却不知道被人把他从哪里找来,站在人群的中间,等着进行唢呐表演。可怜的王腊狗象丑媳妇见公婆一样扭扭捏捏,不小心还憋出了一个响屁,这就引起围观的人笑得前仰后翻。
“大家莫笑嘛,笑痴不笑屁,笑屁不醒事。”广场舞的号头鸭子李爹爹借题亮相了,他的音质和他的舞姿一样干脆利落:“大家听我说,市里呢有个民间文艺比赛,叫我们小区拿个舞蹈节目,当然,你们是晓得的,汪岚是上面点的将,她也是我们小区最拿得出手的招牌,问题是有人举荐罗五千的葫芦丝伴奏,也有人推荐王腊狗的唢呐伴奏,谁最合适,他们两个今天就裁缝师傅打架----试一烙铁了。”
听说对手是罗五千,人们不免怀疑比赛的必要性。原因很简单,罗五千的气场和人场在小区是不容质疑的,即使王腊狗的才艺好于罗五千,谁又愿意冒着风险去得罪罗五千呢?得罪了罗五千就等于得罪了一批人,人家是正儿八经退休干部,又有个当局长的儿子,在小区一言九鼎,在社会上也是父随子贵的人物。小区电梯房周围是不许放任何东西的,否则轻者罚款重者没收,但人家罗五千罗大老爷的电动小四轮就堂堂正正、安安逸逸地停放在哪里,谁敢不服?物业头头说了,等你家光耀门庭了也能如此这般。其实物业头头说得于情在理,上次小区出了安全问题,职能部门要罚款三万,不就是罗五千一个电话的事就摆平了,电话里还牛烘烘地骂个不停。王腊狗何许人也,一个盘了一生泥巴、临老了一月只拿一百二十元钱,还要来城里投靠儿子媳妇吃闲饭、顶没价值的人,他能与罗五千争气场、抢风头?
“吹唢呐,吹......吹是......吹得响的,恐怕白菜萝卜不能上正席哟,还是罗五千大哥有板眼些,要比栽秧割谷我还行。”王腊狗说完低着头,两只手把头发搓的象鸡窝,一张脸憋得通红,不免让人生出怜悯之心。当抬头一看自已站在人群中间,王腊狗慌忙后退了几大步,挨着人群站着,好象这样就避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人们哄的一声又笑了。
这天正好是双休日,草皮上的露水已被太阳晒干,睡懒觉的少夫少妻们也陆陆续续起床到街面上吃早餐了,看热闹的越围越多。忙碌了一个星期的人们,巴不得有个放松放松的去处,那怕是玩猴把戏的也行。
“这德行哪能和罗五千比哟。”
“才人没像,说不定肚子里还真有点货哩。”
两句轻描淡写的话,就象一粒石子投入水塘,搅乱了一动不动的水面,使倒影在水波中一荡一荡地扭曲变形,广场上的情绪也因此波动了起来。
“王爹爹,莫要客套,是公是母拉出来验验就一清二楚了。”
“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,爽快点。”
“莫追哟,唱戏的也要打会闹台锣哩。”
人们耐心地等待着,王腊狗却想拍屁股走人,但被人群围得死死的象堵墙,他想分开一条路,确反被人推了回去,于是改了个方向,又被人推了回去。人们嘻嘻哈哈乐不可支,王腊狗却愁眉苦脸又无可奈何。说实话,如果是在乡下老家,他也许会半推半就,吹一段唢呐又不是下油锅。但这是在城里,一个地域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中心,满街都是高贵的头,到处都是能文能武的人,有乡下人抛头露面的份吗?
“我只当过吹鼓手,上不了台面。”王腊狗憋出了第二句话。
“算了哟,死了屠户不愁吃整猪,莫叫巧。”
“既然来了,学个猫哐狗叫也行。”
“大家安静,听我说,猴子不上树,多打几遍锣嘛,腊狗老弟不多将几次军,是不会拿出实手的。”站在人群中也等着才艺展示的罗五千急不可待地提前进于了角色。由于王腊狗这个宝贝的存在,大家一时把他忽略了,现在一开口,满场安静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。罗五千笑容可掬地拍了拍王腊狗的肩膀继续说:“王腊狗虽是乡下来的,但他的啦叭(就不说唢呐)假以时日也会炉火纯青的,他的象棋就与我不分伯仲嘛,所以,大家莫把鳊鱼看窄了。”
“假以时日”,翻译过来不就是还欠火候吗?人家罗五千多有文化水平,话中有活,笑中带讥,既给对方打了差评,又不得罪人。在他罗五千看来,唢呐不就是乡里的土喇叭吗,哪个还待见这土得掉渣的东西,现在时兴洋鼓洋号,二胡、笛子、葫芦丝才雅俗共赏。
说起棋艺,王腊狗与罗五千未必没有高低之分,只不过罗五千总爱悔棋,王腊狗不舒服。罗五千认为乡里的庄稼还兴挪窝补苗哩,下棋悔一步蛮正常。王腊狗说难怪当官的喝茶学政策,喝酒谈对策。罗五千说你这是看东瓜画葫芦,下棋只能和打麻将比。王腊狗说打麻将也落子算数哇。罗五千说那是因为打麻将带了彩的,下棋是叫化子玩响鞭----穷快活,来不得认真。王腊狗心善总让着他,一来二去成了熟人,当然未成为朋友。王腊狗心里有数,南瓜藤是爬不上屋脊的。
这次文艺汇演,罗五千从骨子里是不希望王腊狗给汪岚伴奏的。一是他认为自已代表的是老城区人的文化素质,输了等于输了码头和尊颜;另一个原因天不知地不知,只有他心知肚明:剧团退下来的汪岚死了爹爹,徐娘半老风韵还在,他呢也死了婆婆,似乎一个锅要补一个要补锅,两好合一好。巧的是这乡下来的王腊狗也是单身只影,时不时汪岚还主动与他谈笑风生,但王腊狗能与他罗五千相提并论吗,就算乡巴佬有这心也没这个屁眼,没房没车没退修工资,和他争风吃醋好比豆腐豆糟分了阴阳的。罗五千看着丑态百出的王腊狗,又瞟了瞟旁边笑而不语的汪岚,心里自信满满。
“王腊狗,吹一个!王腊狗,吹一个!”西边一群人拍着巴掌给王腊狗鼓劲,看那穿的样式就知道都是从乡下来的搬户,多少有点穷帮穷富帮富的嫌疑。
“王腊狗,莫放屁!王腊狗,莫放屁!”东边一群人也拍着巴掌喝倒彩,一看就是罗五千这边的城里人,东风不把西风降,西风就张狂。
“你们欺负人。”有人鸣不平地喊了一声。
“你们还欺负到城里来了哩。”也有人顶了一句。
这是两股世俗偏见的碰撞,不仅产生在这无关紧要的跳舞广场,也形成在生活的意识形态里。在平时,城里的爷爷奶奶嫌弃乡里来的爹爹婆婆土里土气,是文化修养的缺失;乡里来的爹爹婆婆则觉得城里的爷爷奶奶妖里妖气,是满瓶不荡半瓶起波浪的表现。城里的爷爷奶奶认为乡里人占了城里人的生活空间,抢了城里人的码头和饭碗,还使得房价从几百块涨到近万块,没有乡下人,城里人的生活会更阳光;乡里的爹爹婆婆更气喷,农民不种粮饿死帝王相,乡里的环境过去几清爽,天高云淡,河清水秀,都是城里的工业废水、生活垃圾污染了农村,要不是随儿女,请我也不来呢,何况如今的政策改头换面了,乡下人到城里上户口容易得很,你们城里人到农村落户口我看看,不行哩,说明农村户口比城里户口金贵,还牛个么事哟。
小区是个大小区,可比好几个村的人口。刚来小区不久,王腊狗到小区闲逛,看见健身场地到处是人,有的在踏板上练腿,有的在单双杠上翻跟头,有的在吊环上拉身,个个汗流浃背,比谋柴谋米都吃亏。王腊狗心想这还不如拿着锹挖两丈地,背着锄头除两块草,没有半点劳动成果感,吃饱了撑的。王腊狗边看边笑,来到一个荷叶般大的健身转盘旁,象小孩玩玩具似地试着转了两下。
“乡下来的吧?”忽然身后有人问。
“嗯。”王腊狗回答象夜蚊子的声音,毫无底气。
“你们的身体还炼个鬼哟,早炼好了。”
“嗯。”王腊狗满肚子气离开了,心里想念老屋的人,平等随和,亲热得象一个脑壳。记得在河边树下乘凉时,总会有人说,王师傅,吹一段。他也会卖关子,吹不要力气?于是就有人给他递上一支烟,满满地收获感,然后愉悦地吹起他的小唢呐。他也会要求别人唱一段花鼓戏或讲一段古话,不管好与坏,都会有巴掌声,不象城里人这么吃生排外。
人啦,不仅生命脆弱,尊严也是这么难得。要是能象云南的亚洲象那样任意往来,连城里人都以诚相待,该多好。哎!只有夹着尾巴做人,不给儿子媳妇生乱添堵就阿弥陀佛了。正是因为这种心态,一个在乡下原本生龙活虎的王腊狗,此时此刻站在人群堆里走也不是,蹬也不是,前脚换后脚,后脚换前脚,总觉得别扭,空有一幅人高马大的架子,在一群人的眼光下,竟是这样不出众。这正是初春载阳的好天气,阳光撒在身上分外柔和,而王腊狗好象站在三伏天里,耳鬓有一排粗粗的汗,顺着他又方又宽的脸颊淌下来。
“喂!王腊狗,你到底会不会吹沙,莫象个缩头乌龟。”
“这那里是看才艺表演,分明是看猴把戏哟。”
“要不要收费哟?”
“说话要讲点良心,本来王爹爹没见过大场面,你们这一闹,他不更紧张了。”终于有人出来打圆场。
“是哟,人家王爹爹是要脸面的人,不象你们城里人不吃生。”
“你这样说就差火了,言下之意我们城里人就不要脸了?”
“我说的是王爹爹,莫要对号入座,城里人得罪不起哟。”
“安静!大家安静!不要扯野绵话跑题了。”号头的李爹爹赶忙出来救场子:“么事诚里乡里的,一个小区进进出出,说得不亲热了。叫我看,那一个敢说前两代三代不是乡里人?我的父母就是口朝黄泥背朝天的农民,父亲叫八斤,母亲叫荷花,养了个师长儿子,养了个工程师儿子,最差的是我,当了一生的屠夫,白做了回城里人,依你们说,回老家我们弟兄三个就不能同桌吃饭了?就要互相瞧不起了?就要互相排挤了?要不得!”看得出李爹爹是带了感情的,眼角的皱褶挂着一丝不易查觉的泪花。
也许是对李爹爹的尊重,也许是被李爹爹一番话所感触,广场上安静了下来。
“老爸!”忽然一声甜甜地叫,象戏台上小姐唱腔前一声叫板,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。是王腊狗的儿媳妇。
“是...是他们...拉我来的。”王腊狗象学生见了家长,感到给家人丢人现眼了,吞吞吐吐地赶忙推脱责任。
“是我和汪岚阿姨叫人拉您来的。”儿媳妇笑着说。
“啊...,”王腊狗的嘴巴半天才合拢。
“你就大胆地吹,这里又没老虎。”
“不怕我丢人?”
“不怕!”
“......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