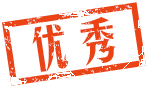|
一
曾峰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,做了两年的泥腿子。本来他还很享受农村的生活,觉得挺安逸的。哪知村里的年轻人渐渐都走光了,不是去深圳广州打工,就是去武汉做生意,最不济的也去县城谋生,他的脸渐渐挂不住了。农村虽好,也非久留之地啊,不是穷死,就是要被那些嚼舌头的用唾沫淹死。恰好二队的亚雄要去武汉做装修,他也会点木工泥瓦活,正好跟着去闯闯。 说是做装修生意,其实就是蹲在汉口顺道街的马路牙子上,等要装修的主顾,等到一个是一个。有的是要做木工,自家打家具;有的是装水电,安木地板的。运气好的话,可以接整个新房的装修,搞一个吃几个月。做这行是靠天吃饭,有活才行。有时一连好几天没活,那心里是慌的一批,房租、水电、通讯费,啥都是钱,只有出的没有进的咋行。 要是梅雨季节,雨下个十天半月,不能出去接活,搞得人心里都是湿漉漉的。情急之下,他跑起了快递。先是兼职,后来一看收益稳定,比搞装修还来钱,干脆做起了专职。快递算是这几年新兴的行业,只要勤快,不怕苦不怕累,养活自己是没有问题,也不再像搞装修那样整天愁眉苦脸,倒适合他的性格。 他住的华安里离汉正街不远,做服装生意的扎堆,外卖快递火爆得很。有时高峰时跑个百把单,都是快递的服装鞋子什么的,腿都跑的发软。但是当躺到租住屋时,盘算一天的收益时,又觉得一天的苦没白吃。 华安里都是私房,有二三层的,也有四五层的,面积都不大,一层也就一二十平米,有的还被精明的房东把一层隔断,做成好几个出租房。早说要拆迁,也一直不见啥动静。这里租客大部分都是汉正街卖衣服的小姐姐,也有当扁担的、跑外卖的。一到下班的点,街巷里弄都是打扮得姹紫嫣红的小丫头,穿的都是品牌大楼的时装,连吊牌都没剪,画着最精致的妆容,睫毛老长,闪瞎了他的眼。 刚开始他见到她们还自惭形秽,觉得高不可攀。可后来几次,他发现有的小妹竟然和他住一栋楼,有的还住他隔壁,也住十来平米的格断间时,他才明白她们并不是如他想象的高人一等,胆子慢慢大了起来。有几次他还试着和她们说话,东扯西拉一番,渐渐熟络起来。她们大多和他一样,来自武汉周边县城,跟亲戚朋友做服装生意。几多年的生意历练,一个个伶俐得比泥鳅还滑。见惯了大场面,做多了大生意,自然也眼界高得望上了天。虽然都同处在一处屋檐下,有时恨不得找他借钱吃宵夜,听说他是送外卖的,言语里还是多少瞧不起他。 曾峰先头还想找个卖衣服的丫头做朋友,觉得两人齐心,攒点钱出个首付,在武汉买个房安家落户,哪知道一丫头听说后“噗嗤”地笑了:“你晓得武汉房子多少钱一平米!你送快递怕不是要跑断侉子。”他网上一搜,心里咯噔一下,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。汉口市中心的房子每平米都破二万了,他猴年马月买得起,怪不得要被嗤笑一番,他是幼稚得紧。 好在他脸皮超厚,抗打击能力超强,也不把这当回事。买不起就不买,先租着呗,卖衣服的不跟,自然有别个跟,难不成打一辈子光棍不成,他就不信这邪。知道这些小丫头的心思,他也省的吃亏,免得花些冤枉钱在她们身上,以为还有啥盼头,一门心思请吃请喝,结果到头来是竹篮里打水一场空。 风里来雨里去,半年不到,他就把这附近的旮旮旯旯混得烂熟。出去多远到江汉路钟楼,往哪拐到已拆迁的花楼街,还有他以前做装修的顺道街,品牌大楼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。华安里则是人世间的一个微缩版,各类商铺药店菜场熟食店等,无一不有,无一不全,生活起居方便得很,怪不得有的人住了上十年都舍不得搬走。 唯一的不足,就是房子太挤。有的间隔就米把远,这家晒衣服,恨不得可以伸到那家去。早上从窗户探出头,可以看到才起的姑娘睡眼惺忪头发蓬乱,揉着眼睛,打着哈欠。见有人偷窥,忙不迭地捂嘴转过身去。也没什么正规的阳台,搭的晒衣架上,衣服如万国旗般飘舞。 有时跑累了,他就提前下班,把电动车放回住处院子里,一个人顺着里弄往汉正街方向走去。他和其他人不一样,别人累了喜欢窝家里刷抖音、聊微信,他则喜欢逛街当休闲。他喜欢摩肩接踵,挨挨挤挤的热闹劲;喜欢观察不同人等,众生忙忙碌碌。也喜欢和街坊嫂子、隔壁男将们拉家常咵天,对巷子里走过的丫头们品头论足。 捉一个好了,免得一个孤苦伶仃,伙计!一天晚上,曾峰坐在巷子边十元理发店外坐着时,一群丫头嘻嘻哈哈地经过,一个嫂子努了努嘴,对他说。 我哪有那福气啊,别个都是大老板。 莫不是曾老板看不中别个。嫂子又笑道。 我看中她,她看不中我。我认得她,她不认得我。天天从这过,几个人他早就烂熟于心了,有二个还就和他同屋。 嫂子要不帮我介绍一个。 当真? 真的!开玩笑不成。假的就请宵夜,撮虾子,成了也请。 说归说,笑归笑,这嫂子过了几天,还当真帮他介绍了一个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