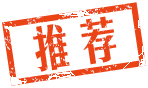针灸是中医大夫治病救人的一种重要方法,几千年来,中医大夫怀揣银针走遍天下,救死扶伤,广行仁义,留下无数的佳话。随着西医的传入我国,人们对于中医逐渐脱去依赖,甚至现在的中医大夫对于针灸的神奇功力也慢慢懈怠,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。尽管现在仍有大专院校着力培养中医人才,但是,学习中医的学子们大都抱有认真学习西医的欲望。按照上世纪通行说法是“中西医结合”,既简便易学,临床也省时省力。拍片、透视、血液化验一目了然,何乐而不为?当然了,一般大病或常见病症,西医显然有其独特优势。然而,许多在西医学上不认为是病症的“病患”,尽管患者倍受折磨,却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。比如关节酸疼、腿脚不灵、厌食、头昏胀,最令人恼火的是不红肿也不发烧的牙齿疼痛。西医最高明的手段是注射一针镇静剂,然后慢慢等待日久拔掉。中医却不这样,简单地用针一扎,立刻奇效,就象从来没有过牙齿疼痛这回事。 我有一同事就有如此遭遇,牙疼到不想吃、不能睡、半夜三更跑到屋外把脸抽得“啪啪”响,大有痛不欲生的模样。天亮到医院,医生不知用什么药水洗了,然后打了一针止痛针算是不痛了。中午饭还没来得及吃呢,牙齿又痛起来,麻木加疼痛,那滋味看到都心酸。后来找到中医大夫扎了一针——就那么一针,立即不痛了,而且过了好几年也没有犯病。神奇的银针如此效验,这是西医无论如何也要望尘莫及。如此简便神奇的针灸,要想真正学到手并非简单。它首先要掌握中医理论,明白人体的经络脉搏分布,明白各个穴位所在位置以及它所肩负的调理范畴,更要懂得用针的深浅和时长。要想掌握这些,就必须全面理解中医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要素,而这一切又都是“气、神、形”的阴阳五行概念,是深奥的玄学知识,谈何容易!这也是眼下实力派的中医大夫凤毛麟角的原因。关于针灸疗病,笔者也有过亲身体验,其神奇到令人终生不忘的地步。
我们村子小学校院外有个池塘,夏天碧波荡漾、烟柳婆娑十分可观,而一到枯水的冬天便显得十分萧条。小时候上学路过这里,发现池塘冰层下有鱼儿游动。水很浅,冰也不厚,我于是脱掉鞋袜下到池塘捉鱼。由于穿着太厚,我一只手提着棉裤,另一只手伸进冰冷刺骨的水中乱抓。折腾了好一阵子,鱼儿捉到不少,手腕也冻得麻木酸痛。从此之后,手腕经常酸胀疼痛,而且时轻时重,重到有时连拿筷子也感觉乏力,看了很多医生也不见丝毫好转。长大参加工作之后,自己又跑了好几家大医院诊治,大夫每次看过之后便针灸,临走给我开几包伤湿止痛膏之类,终究送我一句安慰话“关节炎,不要紧”。
尽管是“关节炎、不要紧”,却是折腾了我十多年。直到有一天,一支部队拉练路过,晚上就驻扎我们单位附近。晚上没事,我和几个同事小伙伴到部队院子里去玩,正好卫生队帐篷有个卫生员值班。因为年龄相仿的关系,我们很快就聊得热闹。卫生员吹虚自己学会了针灸,胳膊腿疼痛扎针就好,我于是便把手腕伸出来让他针灸。小卫生员没料到吹牛吹出难题,犹豫再三,最终还是取出了银针。
他两眼盯着我,就象屠夫打量即将被宰杀的牲畜一般,手里的酒精棉球擦拭银针足足有五分钟。我看出他心内紧张,因而自己首先胆怯了,慢慢地把手缩回来。卫生员看出端倪,精神为之一振,装着很有把握的样子笑道:“没关系,扎进去又不痛。”同行的几个人爱凑热闹,强行把我的手按在桌子上让他扎。此时的我别无选择,心一横、牙一咬,准备让这家伙做一次活体试验。只见卫生员又擦拭几下银针,再次询问我痛疼的具体位置,然后抖抖索索地把银针扎进肉里。当时手腕一阵酸麻,那种难受的滋味无法用语言表达,感觉似乎再碰一下银针就会疼得天崩地裂。
好在卫生员并没“碰”那根银针,而是从针筒里又抽出另外一支要往手腕上扎。我见此情景,心中十分恐惧,几乎是哀求地声音让他不要再扎了。这家伙毕竟是个新手,见我如此紧张,便不敢轻举妄动,只是把扎进肉里的银针捎微动了一下——我的天哪,那种酸麻的滋味别提有多难受!
针扎在手腕上大约有一分钟,按卫生员的意思要过十分再取出。始终悬着一颗心的我让他尽快拔掉,依旧是带着求饶的声调。尽管卫生员有些不情愿,最后还是按照我的要求拔出银针,我悬着的心才算踏实。
针灸过后我心有余悸,并没有顾及手腕疼痛与否,轻轻活动几次倒也没什么不适。一阵紧张过后我们继续聊天,卫生员再也不敢吹虚针灸手段如何高明。
部队第二天出发了,我没再见到那个卫生员,甚至连他姓名也没问清楚。只知道他们部队驻地在浩口农场,离江陵有一百多里路程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次偶尔相遇,初学针灸的保健卫生员一次强迫式的针灸,竟然治好了折磨我十几年的关节炎。无论天阴下雨,还是过度劳累,我的手腕再也没有酸疼的感觉,直到现在,我几乎忘记了手腕曾经的难受经历。
这件事说明,针灸完全可以治好这样的关节炎,只不过在此之前的所有医生都没有真正把握要点。据说穴位是极细微的一个“点”,下针不到位就起不到治疗效果,在此借用“差之一厘、失之千里”的成语也不为过。
卫生员尽管治好了我的病痛,他自己却是糊里糊涂,鬼使神差让他扎准了地方。可惜从此再也没见到那位稚气俊秀的卫生员,假如他知道有这样的结果,那该多么高兴。没有这样一次的偶遇,或者没有几位唯恐天下不乱的小伙伴们,我的“关节炎”恐怕要伴随终生。感谢那位卫生员,不知他后来是否继续从医,是否真的能把“胳膊腿扎一针就好”。提起这个话题,我很有点想念他,恨不能把这个怀揣多年的喜讯告诉他。
|